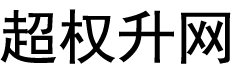怀念旧居小院散文随笔
怀念旧居小院散文随笔
发布时间:2025-01-16 20:21:59
1973年的春天,父亲结束了五七战士的身份,重新回到了城里工作,我的户口也跟着回来。这样,我和父亲终于又成了城里人了。我们住在小镇上的二趟街的一个小胡同里。
小胡同里有着连成排的三个一模一样的四合院,每个四合院内有七间房子。据说,这是原来一家有钱人的房子。我和父亲住在中间的那个四合院。四合院上间是一排五间的大房子,现在看来是倒停房,门是不朝阳的。但由于那房子地处正面,房内的地面是地板,而且炕的墙面是斑驳的瓷砖。由于年限太久,只能看见一点点的痕迹,但依旧很气派。由于当时在城里很难能看到那样好的房子,所以,很让人羡慕的。我和父亲住的是厢房,只有两小间,而且很小很小,共有不到十平米吧。冬天的时候,屋里放的土豆都冻得像石头;夏天的时候,屋里热得像蒸笼。所以,我就想,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住上正面的大爷大婶们那样的房子就好了。
我们小院共住三户人家。上屋住了两家,一家是张大爷家的三间,另一家是段大婶的两间。我们小院的大门是木质的,由于时间太久,已看不出当初它是什么颜色,能看到的只是它木质的本色。大门不是很结实,但是外人想进来也不容易,只有使劲地敲门,我们才能听见。可我们院内居住的人,都能很轻松地从外面把门打开,谁也不用敲门,这个秘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,谁都不会泄露。
张大爷和他的老伴是山东人。听张大爷说,他很小的时候跟人闯关东来到这里学刻印章的。张大爷写得一手好字,在我们这个小镇中,当时所有从刻字社里刻出的印章,上面的字都是出于张大爷之手,因此,大爷虽然早已退休了,但依旧在上班。
张大娘是个典型的贤惠妻子,她的贤惠是今天的年轻人很少具备的。每天,张大爷上班的时候,都是在张大娘深情的目送下离开家的;下班回家时,张大娘总是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。
张大爷年轻的时候是个很帅气的男人,这从他年轻时的照片上就不难看出。而张大娘的一只眼睛却有残疾。每当我逗大爷时,说他这么个英俊人怎么娶了大娘时,大爷总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:“他妈的,那时候结婚前是看不到对象的,只有到了结婚的晚上才能看到。我结婚的那天晚上,等人走光了后,我一掀蒙脸红(蒙在新娘头上的一块红布)——糟杆了(完蛋了)。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,将就吧。”每当张大爷这样说时,张大娘总是抿着嘴笑着,从不为自己辩驳什么。张大娘很能干,特别是很会做面条。因为大爷爱吃,所以她在做面条的时候格外用心。她先用盐和碱化些水,然后再用这些水和面。大娘把和好的面装在一个盆里,再盖上盖子,放到厨房一处醒着。等面醒好后,就开始精心地擀啊擀啊,直到把整块面擀得很薄很薄的,甚至都有点透明了,大娘才放下擀杖,将擀好的面片折叠成扁长形的,再用刀慢慢地切,等把面全切完了,大娘用手把面一抖,只见那面条就像瀑布一样从大娘的手指缝中洒落下来,又细又长。等张大爷一到家,大娘的面条就端到他的面前,再端上一小碟用油炸过的辣椒。每当这个时候,大爷的心情就显得格外地好。
大娘虽然没读过书,但却能讲出很多古往今来的民间故事。什么“白蛇传”啊,“贵妃醉酒”啊,等等,尽管那时我不很喜欢听这些故事,但大娘很爱讲,尤其是大娘在做针线活的时候,总是滔滔不绝地讲,所以我就装出很爱听的样子。其实我并没听进多少,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大娘的针线上了。所以这些故事直到今天,我也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。
1975年冬天,一个特别冷的晚上,突然天摇地动了起来,就听见外面有重物倒地的声音,门和窗同时在晃动,屋里所有的物品都在放出响声。那是让人恐怖的声音。因为我从没经历过这种情形。我吓得抱着头就往大爷家钻,可刚跑到院子才发现,那倒在地上的重物原来是大爷家的烟囱。这时,大爷和大娘也来到院子,只听大爷既紧张又冷静地对大伙说:“别慌!这是地震!我们必须靠着墙边站着,不能到院子中央!”大家听了,都紧紧靠着墙边站着。由于都是从被窝里跑出来的,又很冷的天,不一会儿人们都冻得受不了。在大爷的安慰下,我们都小心地回到家里。但,那一宿大爷是不让我们睡觉的。等到第二天,我们才知道,那是海城和营口的大地震波及了我们。
街道上也根据上级的指示,挨家挨户地宣传晚上不要在家里睡觉。人们只好在空闲的地方搭建防震棚,睡在里面。尽管没有取暖设施,而且还是冬天,但人们还是坚持着睡在里面。我们家的小院里被段大婶搭上金额防震棚,张大爷和大娘每天晚上就带着我来到离家很远的太平乡(当时称太平公社)他们的亲家。他们的亲家住所属于农村,他们就在一大片的空旷的土地中间搭建了一座很大的防震棚,大约能住十几个人。我和大爷一家人也住了进去。那时的冬天格外地冷,由于没有取暖设施,人们互相挨得紧紧的,以此能暖和点。张大爷和大娘那时应该快到七十岁了,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地震棚里挨冻实在是件残忍的事,但也真的没办法。这样熬了几天,我先抗不住了。父亲就用了几个木秆子在家里的炕上搭建一个框架,就算是防震。我终于回家住了。几天后,大爷和大娘们也回来了,不再去外面过夜了。渐渐地人们对地震的恐惧感就减轻了。
夏天的时候,我们的小院是很有情趣的。我们围坐在一起。年轻的在编着自己的辫子,大爷和大娘一边摇着大芭蕉扇,一边争着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。正当我们听得聚精会神时,张大爷经常会突然转了话题:“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,怎么还都不找婆家?这要嫁不出去可就遭杆子了!”每当听大爷这样说,我们就会哄笑地跑开了……
段大婶是个胖胖的女人。她表面上不像张大爷和大娘那样和蔼可亲,甚至还有点严肃,但她的内心是挺善良的。当时她在服装厂上班,每天下班回来还要做饭给她的女儿吃。她对女儿真是很好,望着她每天为女儿忙碌,让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。那时,我们的院里每天早晨经常会来一位卖小蜢虾的老人。老人挑着两水桶的蜢虾,一进到院子就高声喊起来。段大婶往往是第一个走出来,因为她每天都起得很早。段大婶就喊我们起来买,而且还走到院子以外去喊邻居。这时我们的小院子便热闹起来。邻居们纷纷拿着小钵,端着小盆都来了,不一会儿的工夫,老人的水桶就空了。在段大婶的指导下,我们用蜢虾发的虾酱真是好吃,在很长的时间内,每到中午的时候,满院子都飘着虾酱的.鲜味。
段大婶的丈夫是个司机,他的性格很温和,话语不多,总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干着什么。记忆最深的是,有一年大叔从他的单位——庄河陶瓷厂拉回一车废品坛子。大叔自己就用这些废坛子盖了一个厦子,日后,谁看了都称绝。大叔很爱他的女儿,每天当他的女儿上班前,就会看见大叔先把自行车从家里抗出来,再蹲到地上用抹布很认真地擦啊擦,直到自行车铮明瓦亮才停下手,等他的女儿出来后,像是交接力棒似的,将自行车交到女儿的手上……
那时,我父亲总是下乡,而且一走就是十天半月。也不是因为害怕,就是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,凤儿和免儿就喜欢和我做伴睡觉。凤儿和免儿都是张大爷的女儿。免儿是姐姐,凤儿是妹妹。免儿为了自己的名字,曾多次抱怨父母,为什么给自己起了“免”的名字,为什么不把凤儿给“免”了?
免儿虽然比我大七岁,但和我们玩起来没有什么差别。那年,免儿领着我们几个小姑娘坐着敞棚车到大连,半路上突然遇到交警检查,司机吓得马上撵我们下车。我们都六神无主地看着免儿。只见免儿不慌不忙地说:“让我们下车可以,但你们得有一个人陪着我们下车,还得告诉我们你们在哪儿等我们。否则,我们就不下车!”听免儿这样一说,我们的心都放到肚子里了。那个司机一个劲地点头说好。这样,我们就和一个装卸工人一块在金州下了车,大约走了20分钟,就看见汽车真的在等我们呢。从那以后,我对免儿佩服得不得了。
免儿的爱情姗姗来迟,终于在她快三十岁的那年,遇到了她心目中理想的爱人。当然在这之前,有很多的小伙子向她献殷勤,表爱慕,但免儿一个也不动心。记得那年我们县里开运动会,免儿领我去看。在运动场边,一个运动员小伙子为她买了一书包的饼干,免儿不要,那个小伙子就把饼干塞到我的手里,我高兴地接过来。事后,免儿告诉我,那个小伙子对她很有意,但她却对他没什么感觉,所以,就不能轻易接人家的东西。从这件事情上,我也受到了教育和启发,学会了做人的道理。免儿虽然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,家庭的影响也很朴实,但她为人处事却有着自己正直、善良的原则。这是我喜欢她的主要原因。免儿是在冬天结婚的。结婚那天,我和凤儿去送亲,晚上,看着免儿被她爱人的朋友闹洞房闹得哭笑不得,我不由得羡慕不已:什么时候我也能当新娘?
我们这个胡同里共住了20多户人家。其中有个叫小玲儿的女孩当时已有二十多岁,由于身体不好,没有下乡,在街道的小纸箱厂上班。小铃开始患的是肺气肿,后来又患上精神病,但时好时坏。那年我中学毕业了,既没有安排工作,也没有下乡,正当青春的我很是无聊和苦闷。小玲在不犯病的时候,竟像个大姐姐那样来劝慰我,记得她跟我说:“你别上火,要不,我跟我们领导说说,你来我们纸箱厂上班?你别瞧不起我们,我们厂还有县长的老婆在上班呢。”我被小玲的真诚所感动,所以很喜欢和她玩。我家有把秦琴,三根弦的,弹起来很简单。小玲喜欢让我弹给她听,也喜欢让我教她。每天一有时间我就教她弹,很快她就掌握了演奏技巧,而且弹得真不错。可是,有一天,小玲的精神病又犯了,整天整宿地不睡觉,坐在她家的窗台上一个劲地弹琴,一边弹一边扯着嗓子唱,嗓子哑得已经发不出声音还在唱。大量的安定片对她一点不起作用,无论谁劝她都不听。无奈,她的父亲来找我,问我能不能去劝劝小玲,看看是否能有点效果。
我提心吊胆地来到小玲面前,替她擦了擦满脸的汗水。不知怎么,我的话还没出口,泪水先淌下来。看到小玲儿那变了形的脸,我的心很痛很痛。奇怪的是,小玲这次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又打又骂,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我,听话地让我给她擦汗。我轻轻把她手上的琴拿下来,又将她从窗台上搀扶到炕上坐下。还没等坐稳,小玲就一下子躺倒在炕上,眼睛始终不离我的脸,好像在警惕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,也好像是初生的婴儿望着母亲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也不知道说什么,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。半晌,小玲突然说话了:“你哭了?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一把搂住小玲就大哭起来。小玲一动不动地被我搂着,时而还用手拍拍我的后背,好像病的是我而不是她。小玲好了,奇迹般地好了。她的父母很感谢我,说我真有办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让小玲好了,我只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她,不愿意看到她生病的样子。
然而,小玲的命运依旧没有好转。那年春节的时候,我发现小玲很久没出门了,就去她家问。她的妈妈难过地告诉我,小玲在几天前去世了。
胡同里还住了一对特殊的夫妇,他们是盲人。结婚的那天,我们都去看热闹。新娘子坐在炕上,新郎站在地上,倚着柜子在招呼客人。知道家里来人,新娘子就从她手里的小包里拿出一块糖,来一个拿一块,多一块也不给。我们就反复地去,她就反复地给,最后,她的糖分光了,全都分给了我们。
那时我们家里是没有自来水的,都得到公用自来水处去提。我们去提水没什么难的,可对盲人来说困难就太大了。一次,我在提水的时候,看见盲人丈夫也在提水。只见他把水桶放到水管下,摸索着把水龙头打开,接着他就在侧耳听流水的声音。感觉水满了,他又摸索着将水龙头关上,提着水桶磕磕绊绊就走了。由于我们的胡同很狭窄,他提水时晃动的幅度又大,所以,水桶不时地和墙相撞,每撞一下,水就洒出一些。等他把水提到家时,水已经洒得差不多了。看到他们生活这样难,当时正在上初中的我每天放学回来,就为他家提水,一直坚持了一年多。
1979年的秋天,父亲的单位盖了家属楼,我和父亲搬出了生活了七年的小院。在这七年里,小院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和留念。无论快乐还是烦恼,都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,因为它帮助我完成了在成长过程中的人生之课。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邻居们那朴实的关爱、厚道的宽容和善意的教诲。正是这些朴实的东西伴我走过青春,走向成熟。
离开了小院的日子,我的生活有了太多的改变:住上了楼房,结婚生子。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对小院的怀念和依恋。我时常在梦里回到了小院,那里的温馨让我笑醒。当我路过小院时总要进去坐坐,看看老邻居,望望小伙伴,找回那份惬意的感觉。
小院如今已经不在了。由于城市的改造,小院扒掉了,那地方已经耸起了高楼大厦。但小院的影子在我的心里清晰可见,小院里的喃喃细语和朗朗笑声仍在我的耳边萦绕。